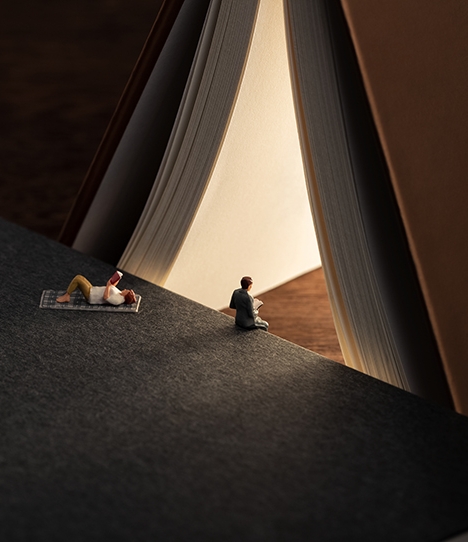一部铁路史,半部家国书。
《青云梯》,是著名作家范稳继《水乳大地》后又一重磅力作,以滇南百年铁路史为经纬,织就了一部磅礴壮美的家国传奇。
从法国殖民者的铁轨撞开南疆门户,到滇人自力修建中国首条民营铁路;从苍茫群山间的寸轨火车,到新时代跨越国境的高铁长廊——这是一条真正的“青云梯”,它承载的不仅是交通之变,更是一个民族知耻后勇、奋起向上的精神史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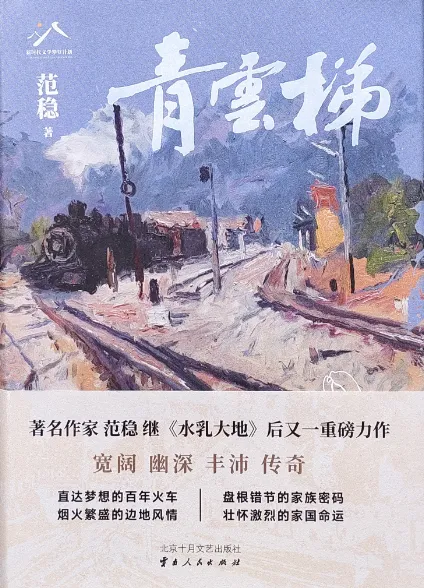
作品融铁路史、家族史、风物史与革命史于一体,宛如一部多声部交响诗。吴、陈两大家族百年的沉浮命运,与云南绚烂的文化风情交织,在历史烟云中熠熠生辉。
愿与您一同踏上这列穿越时空的老火车,驶过百年烟云,抵达家国梦深处。
后记(节选)
这是一部解析一个家族百年血缘密码的书,也是关于一条铁路百年历史的漫长故事。在这个刷小视频看新闻读故事的时代,讲述一段百年故事似乎在冒险,也有些不讨巧。但我还是认为有历史感的故事就像从时间的纵深处驶来的一列火车,满载岁月的传奇。读到它的人,都是它的乘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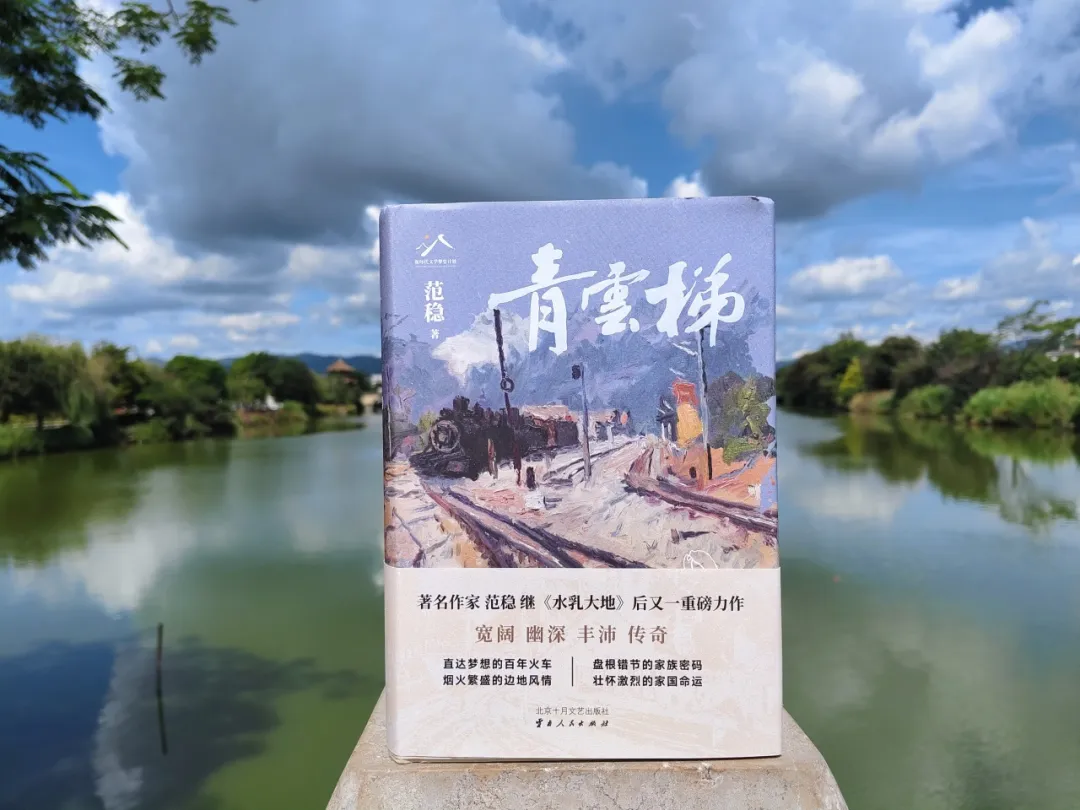
多年来我在云南的大地上“到处乱跑”,我崇尚文化发现式的写作。而云南这片高原有如此丰富的文化资源,正如它“有色金属王国”和“动植物王国”的美誉,它的民族文化也琳琅满目,令人应接不暇。我把自己当一个谦卑的学生,伏下身段向各民族文化学习,也把自己当成一个寻宝者,在丰沛的文化宝藏里潜心开掘。我深信,唯有在云南这片土地上浸淫经年,游遍民族文化百花园,饱尝各民族“百家饭”后,才能对民族与文化,地域和历史,族群及其渊源,有发现新大陆般的喜悦和收获。每一片土地,都在无言地诉说它所养育的人们的过去和现在,也在昭示着未来。
写作这部书的缘起应该在十多年前。二〇一〇年前后,我浪迹天涯打马行到滇南,那时我为创作长篇小说《碧色寨》,关注的重点是建成于一九一〇年的滇越铁路,是不同的文明在这片多民族地区的冲突和演变。上世纪初法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用火车头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这条从越南海防至昆明的铁路,轨距只有一米,俗称“米轨”,但它是当时中国第二条通往境外的国际铁路。由法国人投资修建并管理的滇越铁路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了蒸汽机文明的同时,又傲慢地刺伤了自尊的中国人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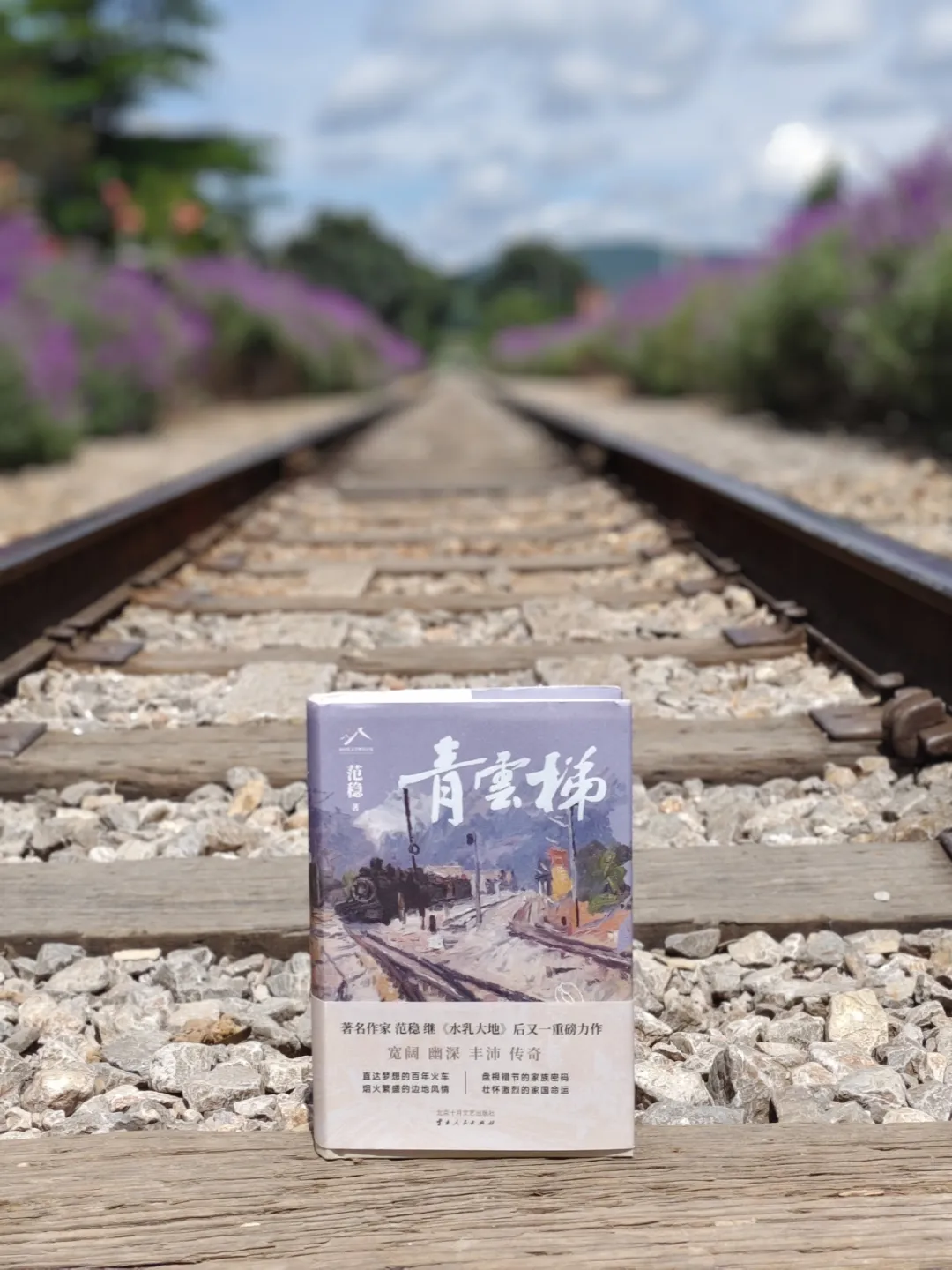
那时滇越铁路沿线所有车站的站长和重要岗位都由法国人担任,铁路就像那个时代的法兰西帝国扩充殖民版图的尖兵。可以想见,在二十世纪初,当一列蒸汽机车头如一头怪兽般闯入这片古老蛮荒的高原时,还在马帮时代的云南人是多么惊讶、惶恐、迷惘乃至愤恨。滇南的人们曾经为反对这条受西方强权保护的铁路,爆发过一次“阻洋修路”的大起义。在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当局的规划中,他们并不满足于将铁路修到昆明,他们的目光还看向了云南各地,甚至邻近的四川、贵州、广西和西藏。十九世纪末,中法已经在南中国边境打了两次战争了,滇越铁路就是中法战争第二阶段的产物。法国殖民部的野心家们还企图通过铁路权的争夺,再挑起中法战争,即“铁路战争”。所幸的是,历史再没有给法国人机会。
我在滇越铁路线上的一个特等大站碧色寨车站采访时,第一次和“个碧石铁路”相遇,它就在法国人建的老车站西端,从站房、铁轨到机车,都是小一号的,轨距只有六十厘米宽,俗称“寸轨”,火车车头像大地上的玩具。两条铁路在这里交会,却不接轨。人们告诉我说,这是在滇越铁路通车仅仅三年后,我们自己修建的铁路。这是一次被打痛之后的奋起一跃,把路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既杜绝了法国人的觊觎,更阻止了他们挑起“铁路战争”的任何借口。“师夷长技以制夷”,云南人也勇于担当。从视火车为“怪力乱神”般的洪水猛兽,到自主修建属于云南人的铁路,在那个年代,有如此勇气的中国人能有几许?当时我站在铁轨上,回望黄墙红瓦的碧色寨车站,再西望同样是法式建筑风格的“个碧石铁路”的车站,感到自己就像站在两个历史的节点上。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在这里迎头相撞,这段精彩的历史必然蕴含着动人的故事。
那时的“寸轨”铁路上已经不跑火车了,但路基还在,铁轨掩没在荒草中,锈迹斑斑,纤细而沉静,像一段正在消失的历史。我当时就想,这是另一部长篇小说的题材,就像滇越铁路和“个碧石铁路”是两条不同性质的铁路一样。我得先弄清它的第一段历史,再来面对它由此带来的某种转变。不过,写一条民族铁路的建设史,以及修铁路的人们,我那时还没有准备好。
云南人对这两条老铁路有着浓郁的情感,或许是因为它们承载了上世纪前半叶太多的历史风云,或许是高原人的铁路梦很早就滋生于漫长的马帮驿道。一个赶马人总是让他的脚底高过一座座大山,但他用一生的时间,也许都走不出高原的辽阔。在云南工作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同轨距的铁路。我没有坐过“个碧石铁路”线上的小火车,它在上世纪末期就停运了。但我确实体验过高原人出行之难,直到二十一世纪前十年,去一些偏远的村庄采风时,还需要骑马。云南的矮种马看上去不够威武,但脚步稳健,耐力好,在崎岖的山路上足可信赖。我经常用一天的时间,只能翻越一座大山。无论是行走在山巅还是坐在马背上,人颇有被大山挤压、重围、望尽天涯路的沮丧。有一年在藏区,我和一个康巴兄弟去一座雪山上的寺庙采访一个活佛,又找不到马。至今他还在笑我说,范老师那天狼狈得看到一头羊都想骑上去。

直到二〇二二年,我感觉到写“个碧石铁路”的时机到来了,那列湮没在历史风尘中的老火车正从大山深处缓缓向我驶来。我再次收拾行囊奔走于滇南。这条铁路像蜿蜒在滇南高原大地上的一架云梯,架在古老的马帮驿道上,架在几座偏远小城的家门前。除了和一座著名的矿山相连外,它并不是一条主干线,但每一座城镇、每一户人家,都有和这铁路相关的许多动人故事。支撑这条铁路的不是雄厚的资本、繁忙的商旅,而是坚韧的文化,是悠久的华夏文明在面对新的挑战时那种知耻而后勇、敢为天下先的家国情怀。而我则像一个探寻者,在铁路的纵深处去寻找过去年代的老火车。
在为《青云梯》做田野调查阶段,我曾经徒步考察过“个碧石铁路”的一段老路基。一百年过去了,这条线路上的一些石砌桥梁还完好无损,有些隧道还可当通道用,深山荒野里的铁路路基上钢轨和枕木早已拆除,路基两旁荒草丛生,山花烂漫,人马牛羊常常借道而过。在走得精疲力竭时,我多么希望有一列小火车劈开崇山峻岭,搭载上我这个天涯浪子。
云南就是这样一个古老的马帮驿道和现代的铁路并存的地方,在一些自古以来就通向高原的峡谷走廊里,你可以一眼望尽这个地方的交通变迁——古驿道、溜索、吊桥、公路桥、铁路桥,以及当下的交通“新贵”高速公路桥和高铁桥。它们像大地上鲜活的交通博物馆,把高原人渴望走出大山的梦想一步步地变成了现实。高铁时代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就翩然降临在这片广袤的红土高原,人们的出行方式瞬间就发生了改变。尚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去北京出差,火车要坐三天三夜。每年探亲回家,走向火车站就像奔赴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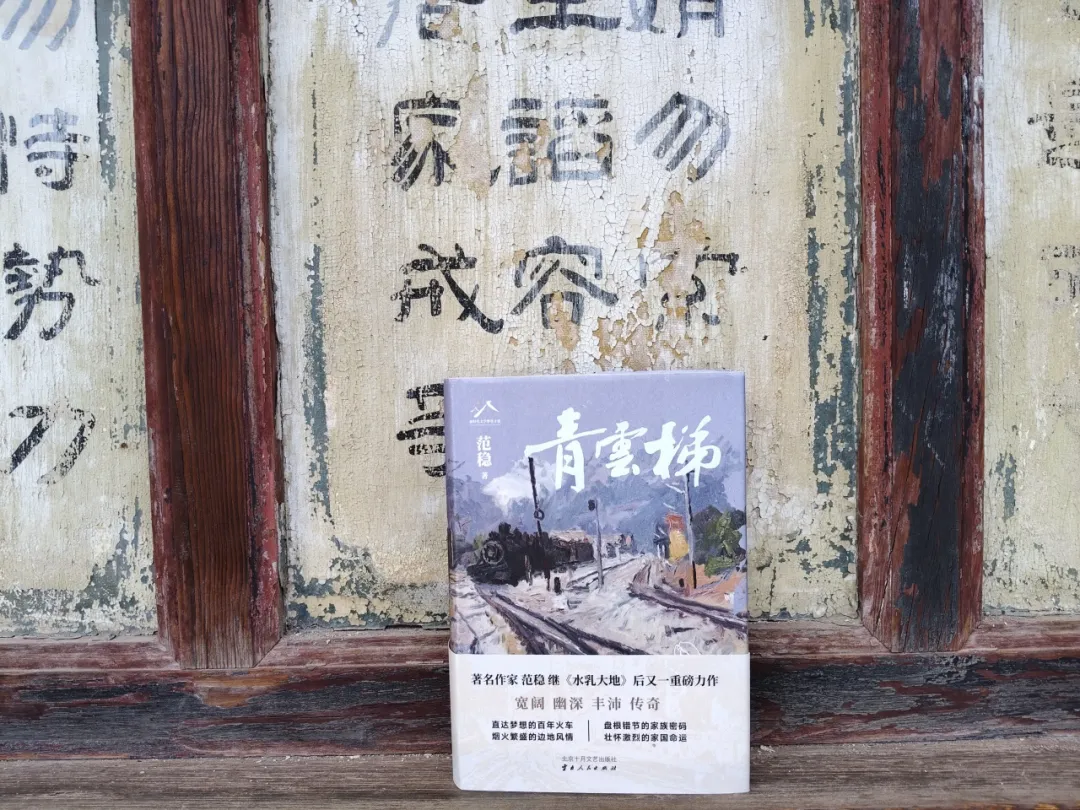
如果我们捋一遍云南这一百年的铁路交通史,就会发现,“个碧石铁路”建成之初,小火车呼啸着驶过尚属蛮荒状态的云南高原,尽管是那个时代的一次巨大的飞跃,但时速仅十五公里;新中国成立后,铁路越修越宽,越建越长,速度越来越快。今天,飞驰在云南高原的高铁时速最高可达三百五十公里。历史的车轮刚好走过一百年。中国人已经把铁路修到了境外,从昆明至老挝万象国际铁路的贯通,意味着南亚东南亚国际大通道的国家战略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云南不再是一个闭塞封闭、被高山大河阻绝的偏远之地。
(本文系《青云梯》后记,作者:范稳)
【相关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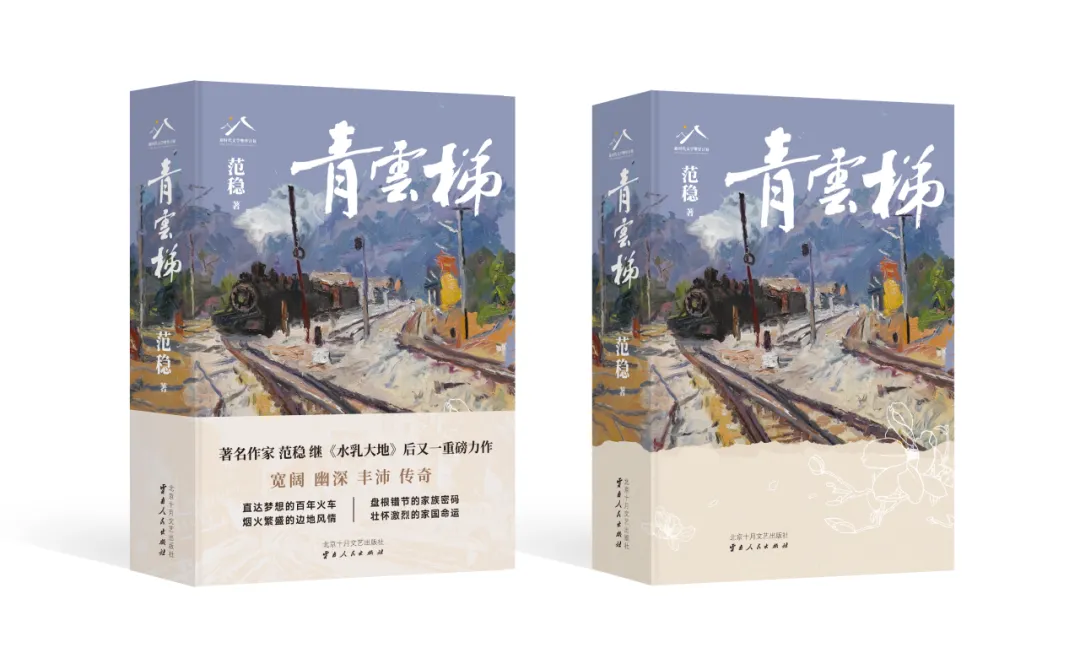
《青云梯》
范稳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青云梯》是著名作家范稳最新的长篇力作。作品以云南高原一百年的交通发展史为背景,展现云南人民立志改变交通状况的历史风云和为此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到滇南人民知耻后勇、自强不息,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直至在新时代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打通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云南人民把铁路修到了境外。高原上的铁路,就是一条通向云端、通往四面八方、通向美好未来的天梯。
作品结构恢弘大气,有丰富立体的层次。它既写了百年铁路修建史,也写了吴、陈两个家族的百年兴衰沉浮史。它同时是一部云南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与风物史,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边地红色革命史。这四个部分水乳交融在一起,构成了一部多声部的交响诗。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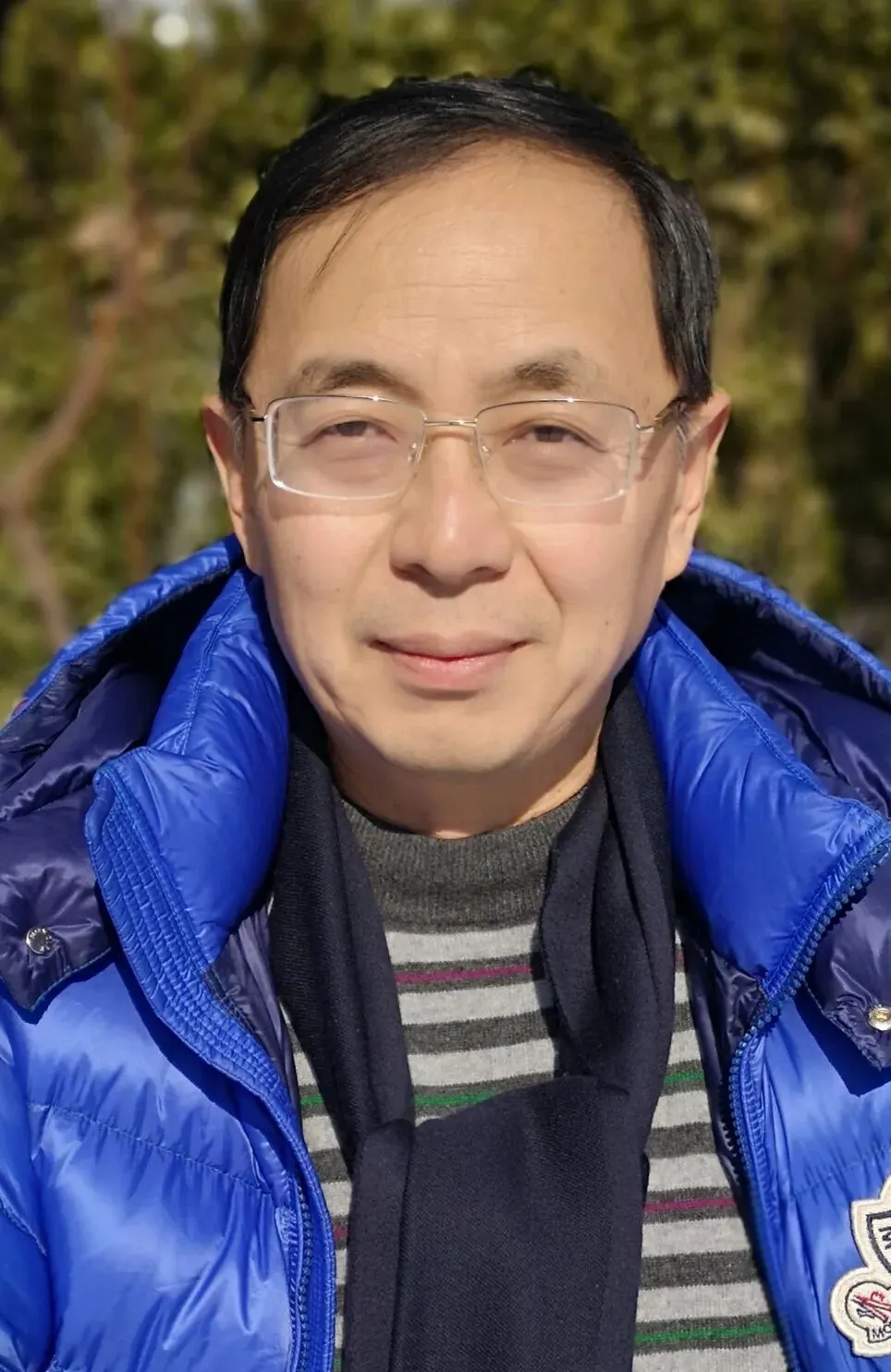
范稳,现供职于云南省作家协会,中国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国家一级作家,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首批“云岭文艺名家”获得者。代表作为反映西藏百年历史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其中《水乳大地》被翻译成法文出版,《悲悯大地》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另一部反映滇越铁路修筑史的长篇小说《碧色寨》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吾血吾土》和《重庆之眼》是其反映抗战历史的两部长篇小说。曾获第七、八、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第八届、十一届“十月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等重要文学奖项。长篇小说《重庆之眼》获2017年度中国好书,长篇小说《太阳转身》获2021年度中国好书。